肖战代言的吃货好物,涉及十大品牌!你都吃过吗?
2024-09-13 15:42:09
上官文露专访《人世间》作者梁晓声:文学具有引人向善的力量
访谈内容提要:
·梁晓声先生首次曝光人物“水自流”的生活原型
·首次在剧中出演角色的感受
·漫谈世界文学&为什么要在文学作品中写好人
2022年2月22日晚上,梁晓声先生的作品《人世间》改编成的同名影视剧正播出到我们这些观众都不愿看到的,周楠见义勇为在美国去世的段落,正歪在床上为剧情流泪,我接到了路文彬教授的邀请和通知,要我与梁先生进行一次对话或漫谈。在此之前,我与梁先生距离最“近”的一次,也就是2021年拙作《人生欢》荣获以梁老师的名字命名的“梁晓声青年文学奖”之时。其余的时间,我仅仅是一个速度颇为缓慢的读者。
近120万字的小说《人世间》我是从大年初一开始看的,一直看到电视剧过半,书也才将近看完了中部,这应该是我读得速度最慢的一部书,不是因为它的篇幅长,是因为我不情愿一下子把它看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牵引着我去细细探究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点都不关乎于故事情节的发展,也无关书里面形形色色人物的大幅度跌宕的命运,甚至也无关那段媒体都在热议的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国并不缺乏史诗级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跨越半个世纪乃至百年的都并不罕见,像《白鹿原》、《平凡的世界》、《走向共和》……这些作品都曾经深深打动过我和千千万万个如我一样的读者和观众,但这部《人世间》让我心灵颤抖,让我如鲠在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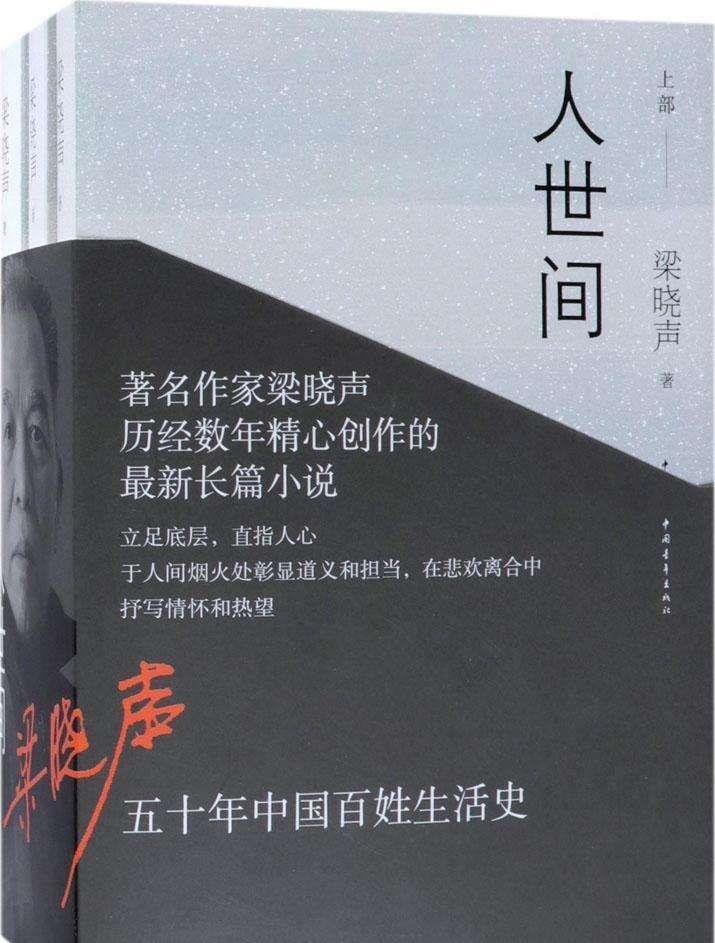
想提问梁先生的问题如坠入万花筒,我几乎迷失。因为电视剧版的《人世间》太火了,面对如此炙手可热的现象级作品,溢美之词一定不鲜见,我不知道于梁晓声先生而言这是否意味着一种纷扰,也禁不住私自地想象他在作品爆红后也会有一些属于他这一时刻的烦恼,这烦恼也许和他每一次写作时的寂寞一样真切。
曾经在作者真实的生命中破败不堪地存在过的光字片为何在如今观众的眼中变得如神话一般值得膜拜?这一条街为何会在评论家笔下变得如此恍惚得几近失真,影视镜头所进行的诗意化的涂抹会否真正给与作者同年代的亲历者们真正的慰藉?
其实那些亲历者们也正是我们,我们的父母辈,甚至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而他们也是我笔下小说的开端和母题。
在我眼中,光字片同样不真实,因为那是我小的时候抓住过的关于艰苦岁月的浮光掠影,我生于80年代初期,那是《人世间》里的周秉坤们开始自己大好前程的开端,那是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能够在一个激荡时代的历史开端降生无疑是具有意义的,所以现在我可以说我对我的童年与少年时期无限留恋和依赖。当看到周楠和冯玥那一身面袋子一般上白下红的校服的时候,我心里涌动的倒不是对青春的怀恋,而是从我降生起到中学为止一直被灌输的“服从”,而服从亦是一种安全,安全感值得眷恋。而安全感也是我在《人世间》所有主要人物中窥见的作者注入的最深邃的思考,也许这是连接我和梁先生之间的一条纽带。
然而,那种安全感从我大学毕业时就荡然无存了。那是一个国家的光速发展在新千年后所呈现出的代价,也或许是每个人的人生青涩与成熟的割裂点,而我总觉得更多的像梁晓声先生一样处在历史深处的人,才能够掷地有声地给出我们一些答案。

面对对梁晓声先生的这次访谈,我异常紧张。从事新闻行业十五年之久,采访本应手到擒来,但今时今日,我已经成为了一名初来乍到的小说写作者,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我几乎没有出过门,梁先生是我两年来接触过的第一位重量级人物。而也许我并非因为和他的“见面”(即使只是电话里的对谈)而瑟瑟发抖,而是因为我终于发现自写小说以来,我已经失去了和人交往和交流的基本勇气。
但在这次对话中,梁先生的友好还是给予了我非常大的力量和慰藉,让我最终可以将它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在以下的访谈录中,我也将不自量力地做一个注解,为我自己也为众多读者梳理梁先生和《人世间》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梁先生荧屏“首秀”的感受,他的作品中“好人文化”的根源,写作的意义等等。

上官文露:
我首先要恭喜您,因为看到了您在《人世间》出演了法官这个角色,因为之前看了其他的采访听说这也是您的荧屏“首秀”,我觉得“首秀”非常成功。那您对您的这次表演是否还算满意?
梁晓声:
这次表演其实是被导演“绑架”的,导演自己也上镜了,剧组里的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很多都被“安排”上镜了,导演本身可能也觉得一般的群众演员还达不到他的要求,他或许是这样想的。当时其实我很冷,虽然是在棚里,但那么大的体育场是没有暖气的,在冬季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又是疫情期间,我很怕感冒。加上配合别人的镜头,差不多也是要两个小时,好在后来宋佳提醒了一下说给梁先生贴上暖宝宝,后来他们赶快找来给我贴上了,就会好一点。我不愿意上镜,但我也不愿意破坏李路导演的好心情。因为李路导演对我不只是尊敬,他同时也对我非常友爱,其实他的这种做法也是一种友爱的表示,所以我会去领会、感受到。

在我问及梁先生看到自己的表演的感受时,他表示他看剧的时候特地跳过了自己出演的情节,这一点令我不禁会心一笑。作为一个曾经以出镜为工作的,如今转向文学创作的写作者,我其实特别能理解梁先生的做法。看以往的访谈,了解到梁先生其实曾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了很多年,也曾经有过知名导演邀请他出演角色,但他都拒绝了,我想这除了是梁先生对于表演艺术的尊重和谨慎,或许还有一种有志于文学者那种天然的“甘于寂寞”。
而且梁先生很幽默地将这次表演戏称为“绑架”,我觉得这种“绑”与“被绑”也是非常温暖的,因为李路导演对于演员的要求众所周知,这与梁先生的甘心被“绑”全都是基于信任、回报情感这些人与人交往之间最珍贵的那一部分。
梁先生身上的这一面,和他的写作中的“好人文化”是一脉相连的。那么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很好奇,这样一个真正言行相顾的写作者,会如何看待“坏人”以及会如何塑造他笔下的“坏人”呢?

上官文露:
那么梁老师我其实在这次采访您之前还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像我们这边有一些年轻的写作者,其实他们有一些问题呢,我觉得倒是可以先来请教您。比如和我同届的韩文易博士,他是93年出生的,他在整部作品看下来之后,对水自流这个人物的印象很深刻。他觉得水自流是一个重情重义而且有情怀的人,再加上他儒雅的形象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这让他会想到武侠小说里“玉面书生”的形象。但是我们也始终难以忘记水自流是曾经属于“九虎十三鹰”的,再加上他始终与骆士宾这种社会人混在一起,也有可能从事过许多犯罪活动。那么您认为读者应该如何看待水自流,您自己喜欢这个人物吗?
梁晓声:
我还比较喜欢。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当时在哈尔滨有一个被打掉的团伙。这个团伙其实并不是我小说中写过的“九虎十三鹰”,它实际上是一个倒卖团伙。但是今天来看的话,也就是一群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要自谋生路,由于没能被安排工作,又不下乡,就靠这种方式来生存。其中有一个人是当年哈尔滨市的建工学院的教师,那么这在当时也算是高校知识分子了。实际上当年听到这件事是在我下乡之前,我是觉得非常震惊的。但我是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抱着团去做那样的事情,那也是一种生存下去的方式。所以呢,当年就是那样的感觉。因为下乡之前我是读过了不少的世界名著的。因此就不太会受当时的政治、阶级等等这种思维的影响去看世事和人,我会不由自主地按照那些作家们的眼光来看。

其实到电视剧《人世间》大结局的时候,我去看了网络上很多人对于水自流的评价,发现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坏人。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疑问,水自流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其实水自流这样一个角色能够得到本时代部分读者、观众的喜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对人认识的加深,因为尊重一个人的复杂性,也就是尊重一个人的完整性。所以对这样的人物的写作,也是非常真实和有力量的。我们不难发现,当今天的观众对在道德上面有一定瑕疵的角色产生喜爱和欣赏之时,可能会产生一种道德上的耻感和对自我的怀疑。而梁先生的回答其实很有助于我们去消化这样的怀疑。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本身就需要我们自己去使用善的眼光,而非其他的,被种种外在的条框加工过的眼光。
而梁先生的这样一种眼光,可以说是在与文学思想的碰撞间实现的。这也给了我们某种重要的启示——文学是我们精神世界的绝佳对手。放眼世界范围内的诸多优秀文学去阅读,或许可以使我们免于个人身处时空所带来的局限。

上官文露:
在这之前我也看了很多书评,说您的作品其实是一种“好人”的文学,那我们从小也是被教育要做好人的,但相信您也看到了在很多80后的书写当中,好人的形象好像被写得越来越滞涩,越来越艰难了。所以您作品里的“好人文化”,正是我觉得您的小说对我来讲最大的魅力。
梁晓声:
我们对好人的标准,第一位是正直,第二位是善良。那么我为什么提出“好人文化”?我就觉得我曾经读过的中国古典文学,欧洲启蒙时期的文学,这些作品里都有好人形象,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也是在讨论什么是好人。启蒙时期的文学,一般我们读的少的话,就会在大概念上认为,那些文学一般是批判性质的,认为它们是在批判社会、批判现实、批判人性现象,但我们认真地去读它们的时候,却会发现,启蒙时期的文学也是建设性的文学。这种建设性的文学就是要使人类进入一个现代人的时期,也就是使人类变得更如自己愿望那样。这一点在俄罗斯文学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他们都非常明确地提出,要为俄罗斯塑造好人形象,读这些作品你会感觉到“好人文化”,会读到这种文学愿望的存在。五四前后的文学也不像一般大家认为的只是批判的文学,呐喊的文学,它也是建设的文学,实际上也是要为中华民族,中国去呼唤好人。无论是我们五四时期的文学还是俄罗斯文学以及英法文学几乎在当时在评论中都明确地提出过“好人文化”这种概念。所以呢,我其实也不是自己突然想到(“好人文化”),而是说在我去回顾世界文学的流程的时候,我感觉到他们曾经提出过的一些愿望,在我们的当下,仍然是可以被拿来的。

在梁先生的观点中,这种带有好人文化观的文学是一种建设性的文学,其中的好人,便是人类如自己愿望般去塑造的形象。
其实如果去回顾的话,可以发现小的时候我们看的书里面几乎全是好人,他们和梁晓声先生作品中所呼之欲出的好人周秉义和周秉坤们面貌相符,课本里、各种故事杂志上,我们时时刻刻会看到那些如雷锋般不畏牺牲的好人。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又被按着头接受残酷的现实了,即好人变得似是而非,变得虚无缥缈,变得待价而沽了,而现实主义文学里也多是对人性恶的揭疮疤,没有自然而然的过渡,我们又被要求适应于恶的多变性了,“洗礼”就是这样地猝不及防。
即使半个世纪过去,50年在历史长河中仍然时日尚青,如今的我们也仍然很难清晰地厘定中国经历的一场从文革到改革的巨变究竟对时代中更迭的青年产生何种影响,但抛开理性的思辨,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内心真实的感受是我们写不出如梁晓声笔下那般的好人了,当然,我们偶尔也尝试进行我们半信半疑的好人叙事,但却因动作僵硬以至于我们自己无法直视,乃至于放弃,那么也许是我们笔下时间的蓄力还不够,不够把他们澄涤成好人?

上官文露:
梁先生您觉得如今这些年轻的作家他们有可能在现实中去承袭您的“好人文化”吗?您应该也知道社会上的这种风气,现在的时代像您自己也谈到过它是那么嘈杂。可能我们身边的好人似乎也变得少了一些,那么我们书写的素材又在哪儿呢?
梁晓声:
实际上我们的好人并没有变少,是生活形态变了,是我们自己主观的眼睛变了。它首先是这样的,这要看一个文学创作者怎样看待文学这件事。你如果仅仅把他当成职业,那就和其他任何挣钱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那就会变成我去考察人们愿意去看什么,人们想看什么,接着就会变成市场需要什么。因此你也会学习经验,那是市场创作的经验。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文学理念。我是因为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受启蒙时期的优秀文学的影响,所以我越写的时候就越会叩问自己,自己从事的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他就是一般的职业吗?就负责带来稿酬吗?说句实在话,在稿费很低的时期靠写作挣钱还是一个笨方法,对于纯作家来说如果不能市场化,也不能带来很大的商机。然而你又写了那么长时间,所以意义究竟是什么?在疫情期间我又回过头去把少年和青年时期读过的优秀的名著都几乎又从头读了一遍。我发现所有的这些文学它之所以是优秀的,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它实际上是有两面的。一面是现实中的人是什么样子,还有一面则是现实中的人应当是什么样子。

梁先生对于年轻作家不愿意触碰好人题材的事情是有一个很敏锐的看法的,我们可能都忽略了从创作到作品面世这个过程中的市场导向作用。理想主义式写作的市场无疑是略显惨淡的,今天的很多写作者可能更倾向于将自己打造成一个“自媒体”,抓住当下的热点,复现生活的暗面,或许由于催逼着的时代节奏、内卷、一夜暴富的神话这些现代产物,这种市场导向的写作几乎成为一种惯性被刻在了很多人的身体里。
然而在梁先生从事写作事业的并没有很多市场红利的时期,虽然一篇文字换不上几两金,但或许却使他身上幸存了一种我们今天缺乏的沉淀与深思,所以今天我们能听到梁先生讲一个写作者叩问自己写作的意义,也无疑是一种幸运。
首先,我想每一个文学创作者都要思考的是,文学是什么?这个我问题我倾向于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提出的见解,他认为文学不存在一个永恒的固定的答案,对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但同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认为每一个写作者在写作中都会获取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梁先生所说,文学是生活之镜,反照生活的同时也呈现生活的理想。所以我们能够理解梁先生为什么不遗余力地去书写好人,这固然有时仅仅是一种理想,但如果连理想都不去往云端上去塑造的话,那现实是否可能会低到现实之下?那么试想到时我们将会面对一个怎样的世界,嗤笑理想的人最终是否还能轻巧地牵动他们的嘴角?对此我是保持疑问的。
梁先生在对谈开始之前其实就向我说明了谈话中可能会有比较不适合去触及的问题,甚至对我戏言可能除了这些问题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但是我完全理解这是一个低调谦逊的作家对羽毛的珍护,其实分享到这里梁先生已经延伸了很多,尤其是梁先生还在感冒中,我真的非常感激。

21世纪20年代,当后现代主义的幽灵将当代年轻人笼罩住,他们一方面享受着娱乐和消解的快感,自以为是地抖着“机灵”,一面不自知地在其中逃避一切的严肃和伤痛。前些日子你还看到他们拿家暴当玩笑戏谑,过些日子也就会看到有人在拿战争开玩笑,玩梗,在一些最极端的事件面前,我们终于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个世界已经被亵玩到了什么程度。
在理想已经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在正能量几乎等同于鸡汤的当下,梁先生的力量是巨大的,其作品的价值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不仅仅是怀旧的诗意,而更是一剂强心针。我对梁先生的一段话印象很深刻:“人性的高度,无论放在多高的位置上,都不显高,也不羞耻。我每次重读雨果笔下的冉阿让,屡屡感觉人性崇高得很不真实,以雨果的智商,他为什么还是那样写,肯定是明知在干理想主义的事,还是要这样写。”其实这里面说到了两点,一是当下缺少对于好人的书写,作家们宁愿去“写他人即地狱”,以挖掘人性之恶作为自身的深刻的象征。(这里也是借鉴梁先生的说法)。二是,其实对于一些非常崇高的形象,我们难免也会觉得不真实,但这正是文学创作所肩负的理想主义的使命。
也许如今我们都不想让自己显出一种理想主义式的天真,因为无数人都会手持无数反理想的实据排队等着耻笑你,所以我们选择了相对“狡猾”的方式,做一个揭露者,用挖掘丑恶以将自己与深刻和复杂划上等号。
但其实梁晓声先生的作品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模版,一个不僵化、不脸谱化地书写善良的模板。如果时代有梁先生这样的写作者站在身后,为我们注入勇气,可以使我们拍着胸脯去书写善面,而不仅仅把揭露人性的恶当成一种摩登,我相信将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敢于去书写人性的光辉,不再惧怕笔端会流露出假面和僵硬。
写作(应该说是单一、纯粹、孤注一掷的写作),犹如坐上了一列不知方向的列车,而每次开始一部新作品的创作都犹如这趟列车行驶进了一条山间黑暗的隧道之内,直到写完和改完这篇作品的最后一个字,列车才找到洞口迎来光明。2020年是这辆列车的“始发站”,从这一年出发,我们开始在腾讯音乐这片多元化、开放性的土壤上行驶。这不仅是我们每个个体的列车,也是文化传播的时代列车,然而我和聚集在这里的其他写作者有一个共识——妄图用文学的声浪盖过时代的喧嚣。而这也正是写作者的寂寞与辉煌,只不过这寂寞是关乎自己,而辉煌更是只属于自己,无关他人的评价抑或喝彩,因为那是写作者自己在一部作品中和他笔下的角色一起找到了一条新的人生之路,寻找路径即是写作者的辉煌。
和梁先生对谈的那天夜晚,终于结束了连续多天的写作焦虑,感觉犹如爬出烟囱,抖落一身灰尘,只留下余暖。我想我的这辆列车将像仿佛无法通晓寂寞一般地,永远在隧道里行进,直到我终于借够了理想主义的气力,能够顺畅写出光辉的人为止。
受访者简介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49年9月2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祖籍山东荣成市泊于镇温泉寨。他曾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及影视作品,为中国现当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现居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1968年至1975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劳动。1977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1988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厂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2002年,开始任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9年7月,获第二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8月16日,凭借作品《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9月23日,长篇小说《雪城》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2024-09-13 15:42:09
2024-09-13 15:40:02
2024-09-13 15:37:55
2024-09-13 15:35:48
2024-09-13 15:33:41
2024-09-13 15:31:34
2024-09-13 15:29:27
2024-09-13 15:27:20
2024-09-13 15:25:13
2024-09-13 15:23:06
2024-09-13 15:20:59
2024-09-13 15:18:52
2024-09-13 15:16:44
2024-09-13 15:14:38
2024-09-13 15:12:31
2024-09-13 15:10:23
2024-09-13 15:08:16
2024-09-13 15:06:09
2024-09-13 15:04:02
2024-09-13 15:01:55